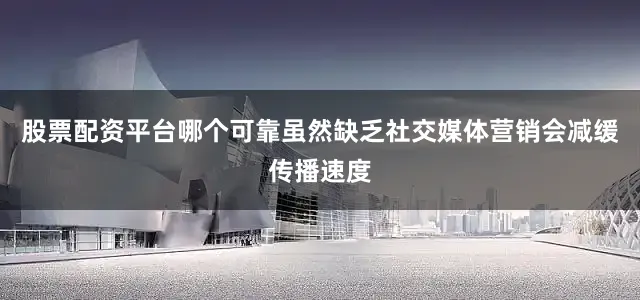9.4 的华语剧王,第二季跌到了 8.2。
崩了?
目前已经完结,没有如 Sir 的预测那样,复制上一季的爆火。
但评分也恰恰爬升到了 8.4。

《我们与恶的距离 2》。
追完了的 Sir 仍然要说,这是今年最被低估的一部华语剧。
开篇节奏缓慢,人物众多,故事线庞杂,时间跨度大且采用跳跃式叙事。
这些无疑在挑战观众的耐心与记忆力。
但它并不追求做一部爆剧。
而是挑战更禁忌、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因为前几集"看不懂"就打低分,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今天 Sir 想要带你来看到它的全貌。
要为杀人犯辩护吗?
"为杀人犯辩护,岂不是等于洗白?"
Sir 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但是,真的如此吗?
不妨先来看看《与恶 2》的最后一集,一场法庭审判戏。
更准确地说,是一堂我们缺失的法律教育。
被告人:胡冠骏,超市纵火案的元凶。
案发过程——
与超市店长发生争执后,一气之下,他朝店长的机车泼洒机油。
随后,点燃了打火机 ……
蔓延的火势,席卷了超市。
五人死亡,十二人受伤。

放火、烧车、有人员伤亡。
这不是板上钉钉的死刑?
为什么还要为被告辩护?
辩护律师要为被告脱罪吗?
并非如此。
辩护律师当然知道,被告有罪。

△ 这次的辩护律师,依然是吴慷仁所饰演的王赦
但他依然要站出来——
一,杀人犯也有人权;
二,这是必要的程序正义;
三,比起灭杀"恶人",更应该了解"恶为何产生"。

王赦的出现,还并不只是为了"政治正确""保障人权"。
这一场庭审,也不只是执行程序正义,或是平复民愤。
他的辩护,他的质疑,检察官与他的辩驳,受害者家属的不同诉求,加害者的人生经历,加害者家属的痛苦与愧疚 ……
这些都在撬动我们大脑里的思想钢印,也在让更多社会潜在风险浮出水面。
来,让我们先沉浸式进入这场庭审。
第一个问题,判什么罪?
这关涉的,是胡冠骏的放火动机问题。
检察官认为,这是预谋杀人罪。
胡冠骏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出了放火的行为,并导致了人员的伤亡。

王赦反驳,这是放火烧毁他人物品,过失致死罪。
胡冠骏放火的本意,只是烧店长的机车。
这当然是犯罪,但不至于到"预谋杀人"的程度。
火势的扩大化,与大批人员的伤亡,还源于超市前门堆积的易燃物,和后门故障锁死的安全逃生门。

悲剧不是一个人酿成的。
匆忙地定罪,是不是一种集体的甩锅,并为下一个悲剧继续埋下隐患?
第二个辩论的议题,是否要因被告的精神状况而减刑?
这关涉的,是社会要不要给胡冠骏一个机会。
经过精神科专科医生鉴定,胡冠骏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注意,反社会人格,不完全等同于杀人倾向。
而是个体长期处于严重焦虑、抑郁的状态,挫折忍受度低,容易有情绪起伏,会采取冲动不合宜的攻击行为。
这源于他童年时期分离焦虑导致的 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以及缺少恰当的、系统化的家庭教育、长辈关怀和医疗支持。
换而言之。
如果他能得到家人、社会集体的理解和包容,与长期的医疗保障。
他会不会有教化成功、重新做人的可能?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也是一个可实操性问题——
给胡冠骏减刑,并且提供相应的措施,有可能会看到一个人改邪归正。
有人直呼"这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残忍"。
检察官与部分受害者家属,坚持认为要判重刑。
不然,没法给无辜的冤魂交代。
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这是他的错
要他负起责任
请给位国民法官
给这些死者一个交代

但也有受害者家属,选择了"后退一步":
我永远无法原谅这个人
但是我也不想杀人偿命

既是觉得,胡冠骏的命,无法抵过自己妻儿的命。
也是因为妻子牛祐荷生前的话:
我们做旁人的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该做的理由
我们就不应该放弃
我们就应该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是,或者否?

最后一道题——
是否要判被告死刑?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生与死,就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要他死,还是要他活?

是谁在培养杀人犯?
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父母、家庭、学校、社会、天生坏种?
对此,《与恶》系列从来不会"不懂装懂"。
更多的,是呈现,并且在呈现中向观众抛出问题。
第一季,它瞄准的是,事发后加害者家属的愧疚、自责,与不解: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杀人犯?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要花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第二季,它更进了一步,纵横交叉着深挖培养出杀人犯的土壤。
其中,尤以胡冠骏的经历最为详实,对胡冠骏的成长进行了持续跟踪。
可以说,这个过程,《与恶 2》在进行一场十分立体的教育实验,而不是简单化、标签化、扁平化。
胡冠骏,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有一个哥哥。
6 岁前,跟着外婆生活,是一名留守儿童。
6 岁时,被父母接了回去,出现了分离焦虑情绪。
经过医生诊断,患有 ADHD,症状以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为主。

一开始,母亲很重视——
她给孩子吃药,寻找能培养专注力的兴趣班。
但是,父亲大发雷霆——
小孩子都调皮、不听话,吃什么药!
等孩子上学后,发现孩子的成绩跟不上同龄人,父母从着急,到崩溃,然后破罐破摔。
剧中有一幕令人印象难忘。
母亲辅导小胡冠骏做作业,发现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后,气得把他锁在阳台上。
阳台外,孩子在哭,在仇恨;阳台内,母亲也在哭,也在仇恨。
互相都处于一种痛苦、抑郁、敌对的情绪当中。
这一幕,便是胡冠骏的成长常态,也在加重他的 ADHD 症状。

很长一段时间里,胡冠骏是一名"精神孤儿"。
他没人管,没人理,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给人"闯祸精""不良少年"的印象。
直到遇上牛祐荷和马亦森。
牛祐荷,少年调保官;马亦森,精神医师。
在他们的引导与帮助下,胡冠骏也曾改变过,自救过,学着控制情绪,学着跟父亲沟通。
胡父同样地,重新学习如何当一名合格的父亲,跟儿子一起生活。
但,并不是所有的和解,都会迎来大团圆,而是会造成彼此更决绝、更破碎的分裂。
缺爱又敏感的儿子,和霸道又独断的父亲,再一次分开。
胡冠骏,再一次成为"精神弃儿"。
直到儿子闯下弥天大祸,父子俩才再次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说,谁是恶人——
从父母到孩子,从学校到社会,每一方都尽其所能地付出努力,而胡冠骏,也并非是"天生恶种"。
怎么还是一步步滑向悲剧?
怎么社会还是养出了一个"杀人犯"?
是不是早一点介入,会更好?是不是不中途放弃,就能避免?
《与恶 2》没有给出一锤定音的答案。
正如现实里的未成年人教育与亲子沟通,时时刻刻都存在着难题与挑战。
教育,是一项马拉松长跑。
不是一次长谈、一次和解、一次拥抱,便能高枕无忧的。
只是,我们常常忘了一点。

要把潜在杀人犯逐出社会吗?
既然难以从根源上杜绝。
那么,能不能防患于未然,将"潜在杀人犯"赶出去、关起来?
比如,胡冠骏这样的"反社会人格";或者,发作时难以自控的精神病患者。
不必假装正确与人道,这的确是大众的隐忧,甚至是期待的解决方案。
就像这个豆瓣提问:
社会是否应该允许胡冠骏这样的人的存在?

《与恶 2》也不掩藏大众的担心与害怕。
就像剧中康复之家选址的情节。
普通的民众,都在强烈反对:
万一跑出来伤人了怎么办?

《与恶 2》也不将精神病患者,包装成无害的傻白甜。
相反,它甚至多次出现了精神病患者伤人的情节。
一次,是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出租车司机,在病发时捅死了警察。
另一次,是有躁郁倾向的破产老板,在车上拿刀威胁妻子,结果与妻子、儿子一同车祸丧生。

污名化精神病患者?加重大众的恐慌情绪?
非也,《与恶 2》是在正视精神病患者的防治问题。
每一次出事,几乎都因轻视与忽视——
患者轻视病情,拒绝吃药;家属忽视异样,没有及时处理;
社区、医院乃至于社会轻视病情,没有及时送药、没有及时关访、没有完善医疗体系。
往往等到不受控的时候,才有人跳出来处理、声讨、审判。
于是,大众总是看到,犯错的精神病患者,却看不到出了错漏的社会相关体系。

而且,在精神疾病常见,心理问题泛滥的当下。
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有一天变成精神病人呢?
我们总是忘了。
"精神病人",在生病之前,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正常人。
他们不是天生恶人,更不是与生俱来的"精神病""杀人犯"。
他们往往是因外界的压力与创伤,突破了心理防线,导致情绪的失调,与精神的崩溃。
看似在正常生活的人,内心又是否完全纯白无暇?
就像马亦森。
妻儿被害后,他独坐着,都会落泪。
看到抢救场面,他会惊恐症发作,整个人蜷缩一团。
得知胡冠骏即将出现,他心里盘算的,都是如何杀人。
他的大脑里,似乎只剩下最后一丝理性,来阻止他的失控。

《与恶 2》,没有将他塑造成完美圣人,同样正视他心中的恶。
因为人性当中,本来就有恶。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群体的问题。
而是存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的人性深渊。
隔离了"恶人",驱逐了"恶人",假装恶便不复存在。
这才是最大的恶。
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
就像胡母将小胡冠骏关在玻璃门外——
这也像我们,与犯下恶性事件的人。
互相愤怒,互不理解,将彼此都视为仇人、恶人。
结果永远是将问题悬置,将情绪蔓延。

《与恶 2》的终极拷问在于: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在于它能多么高效地驱逐"深渊边缘的人"。
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照亮深渊本身,并奋力构建不让普通人轻易滑落、以及滑落后能被稳稳接住的堤岸。
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的运作的体制
可以去"接住"
每一个在往下坠落的人
其实整个《与恶 2》在做的事情
就是"社会安全网"

而这,或许也是剧难以爆火的原因。
因为今天的主流情绪——
一方面凝视恶,欣赏暴力奇观;另一方面再反杀恶,作为一种自我麻痹的放松。
"恶",永远是他者的。
好像我们只要不断地铲除、铲除,就够了。
唯独不愿意看看,恶到底是怎样生长出来的。
我们与恶的距离。
其实,更是我们与诚实的距离。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反思自我的八宝粥
广盛网-配资安全配资门户-散户配资网站-实盘杠杆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